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根据母亲的回忆录写的这篇文章,入选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弘扬抗战精神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征文”,刊登于8月13日《中红网》;同时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共常熟市委宣传部、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共同举办,由《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作家文摘》支持的“沙家浜精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
在那段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14年里,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所有抗击日寇的国军将士都是值得讴歌的,而无辜百姓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甚至惨遭杀戮,也是绝不能被忘怀的。我们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就是不让那些悲壮血泪不再重演,这是我母亲,以及他们那代人所希望的,也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坚持,并告诫后人的。这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初衷。
原文为《母亲叙述的往事》,刊登于“共识网”,本文作了节选。 母亲生于1919年9月19日,特别好记。但母亲总说是“9.18”的第二天,看来那组数字对母亲更加刻骨铭心。 母亲已经离去多年,我思念她时就会翻一翻她的回忆录,其中记录最多的是抗战时期的经历。 逃离战火 1937年,17岁的母亲从镇江女子师范毕业,被镇江私立培初小学聘用,就待暑假后开学便可以走上讲台了。正当妈妈为能当上一名教师而高兴的时候,“8.13”淞沪抗战打响了,整个长江三角洲都处在危急之中,日机时不时地飞来盘旋几圈,镇江城里人心慌乱,百业具废,妈妈的教师美梦自然烟飞灰灭。那时我外公还在西安公干,无奈之下身怀六甲的外婆只得扶着太婆,带着我妈和大姨、大舅、小舅,顺着惊慌失措的人群开始了逃亡。 当时富裕人家乘大船,或轮船往九江、武汉、重庆等地跑。贫困人家则拖儿带女徒步走。我外婆还算有几个小钱,就和另一家合租了一只木船,带上二床被子和几个包袱,在苏北的大运河里漂淌了五天到达兴化。 当时外婆的意愿是设法去到徐州,再乘陇海线上的火车,奔西安找外公去的。 兴化县城不大,四周环水,都以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逃难的人蜂拥而入,街头巷尾到处是难民,都在寻找住处,很多人只能借人家客堂一角搭张铺安顿身子,还有不少人借人家的柴房居住。外婆一家赶到兴化时,已经连柴房都借不到了,最后在远离县城一个偏僻地方发现有座尼姑庵。托庵里妙静师太的福,一家人有了个栖身之地,但庵堂岂能久住,更何况外婆即将生产。后来,师太出面介绍,附近一户人家,在堆杂物的偏房里腾出一块地,临时放下一张床铺,外婆就在那儿生下了我小姨。 外婆产后仅只几天,国军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兴化城里的人坐不住了,又纷纷外逃。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外婆不顾产后虚弱,毅然决定再次上路。我妈是老大,外婆不便期间,大情小事都是她打理。母亲四处打探,找到一条装货的木船要往徐州去,谈拢价钱后,全家人登舟离开了兴化。 木船航行了两日,发现大批人群反向而行,一打听,说报纸登了徐州告急的消息,这会儿大概徐州已经失守啦。 去路已断,木船只好调头后转。险境中,人们已经顾不得身份,外婆一家和船主结成患难之交,互相之间不再讲什么价钱了,有东西大家吃,有力气就一起摇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逃到安全的地方去。就这样,外婆一家乘坐这条船沿大运河往南,途经东台、如皋等地到达南通附近的天生港。此时,上海早已沦陷。有道是最危险的地方或许最安全,我妈的三表舅——我应该叫三表舅公——托人捎来信,说上海的租界里比较安全,让外婆带家人赶快到上海去落脚。于是,外婆又扶老携幼辗转来到了上海。三表舅公在英租界靠近四川路的背街小巷内给外婆一家找到一间六平方的亭子间,仅搁一张床,一家老小就蜗居在这小屋里度过了初到大上海的时光。 逃离日战区 外公不放心颠沛流离的家人,辞去公职寻找安身立命之地。那时,上饶远离战区,受“赣南新政”辐射,抗日救亡的风气很浓,外公觉得是正气抬头的地方,于是决定把家安在上饶,托人带钱带信到上海,要外婆带上家人,快快离开日占区。 那时候,国统区到敌占区十分困难,据说要过三道封锁线。外婆接到信和钱已是38年的春夏之交了。 同样,从敌占区到国统区也非易事。经三表舅公多方托人筹划,才定下迂回曲折的行程。 外婆带着一家老小登上开往温州的轮船,在海浪中颠簸了几日,直到吐光了胃里所有的液体,才到达温州。温州多皮货和海货,外婆囊中羞涩,孩子们只有饱饱满眼福的份。 一家人在温州街头转了二天,才找到三表舅公托付的人。第二天,那人将外婆一家送上汽车,车过蒲田,夜宿青田;次日清晨再出发,经丽水、永康,到金华。下得汽车,外婆抱着小姨,领着小舅坐在马路边看护着包袱行李。我妈和大舅去火车站购票,幸运地买到了当日的火车票,这样就免得再露宿街头了。火车途经衢县、玉山。太阳再度升起的时候,才平安驶进上饶站。 一家人在经历了胆战心惊的逃难后终于团聚了。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在日寇的铁蹄下,老百姓哪有自由出行的权力! 再度逃难 团聚了,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为了让家人生活得好一些,外公不得不外出经商。 上饶城池不大,是第三战区所在地,浔饶师管区(包括江、浙、皖、赣)的各师都在上饶设有办事处,因此满大街都是军人。 自从九江、南昌沦陷后,江南的时局格外严峻。只要天气晴朗,日机随时会来骚扰。大家一听到警报声就飞快地躲进防空洞,有时一呆就是一天,到晚上才能回家做上一顿饭。只有下雨天日机才不出动,因此大家都盼望天天下雨。 不久,日寇近逼金华,人心惶惶,三战区各部也准备转移。外婆和母亲着手准备再一次逃难。就在这时,大表舅公夫妇俩从安徽逃难到了上饶。外婆让他们休息两天后再一起走。 外婆让母亲雇了架板车,拖着衣物行李和太婆,一家老小并大表舅公夫妇一道跟着行走。三战区大批汽车,载着人员和辎重,沿着上饶到崇安公路撤退。难民们也跟着往崇安方向跑。逃难的队伍跑过铅山县,翻越武夷山,到达福建崇安。外婆和太婆、大表舅婆都是小脚,走远道实在不便,太婆说还是歇歇脚再走吧。大表舅公打听到一家货栈阁楼上可以住人。跑去一看,阁楼上堆着好多杂物,能容人栖身的地方很小。于是大表舅公夫妇俩就暂住小阁楼上,外婆把一时不用的衣物包裹留在阁楼上,带着太婆和孩子们在城外另找一间民房歇息。 金华失守的消息传到了崇安,说上饶也保不住了,大家都在庆幸自己走得快,否则就出不来了。 亲人遇难 无情的灾难还是降临到崇安。第二天,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在全城响起,人们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街上的人近的躲进防空洞,远处的往郊外的山沟里跑,有的慌不择路往村民的草垛里钻。 日机扔下了几颗炸弹扬长而去,城内顿时浓烟滚滚,火舌升腾,人们顾不得许多,赶忙跑回城里看看自家有没有受损。母亲一下子就想到大表舅公和大表舅婆,对外婆说:“我先去看看。”说完就往城里跑,我大舅也紧跟着跑去。他们赶到货栈,货栈已被炸成一堆废墟,塌落的房梁还在燃烧。母亲和大舅冒着呛人的浓烟冲进废墟拼命地呼喊,但什么也没找到,只看到放在阁楼上的衣物和被褥已散落在废墟里,变成了灰渣。这时外婆也赶来了,母亲就拉着外婆去找防空洞。可是防空洞也被炸塌了,好多人在往外抬人,有的被炸断了手脚,有的炸伤了身子,全是血肉模糊的样子。空地上已经排列着几具尸体,母亲忐忑地搜寻着每一个伤员和每一具尸体,终于看到大表舅公已躺在那些尸体中了。大表舅公的尸体是完整的,脸色发紫,说明是防空洞被炸塌后闷死的。但是没有见到大表舅婆的尸体,大家又四处寻找,结果在一枝树杈上发现一只裤管在随风飘荡,母亲认出这是大表舅婆的裤子,接着在稻田里找到一只大表舅婆的鞋,最后才找到被炸飞老远的缺了一条腿的尸身,其惨状令人毛骨悚然。外婆更是痛不欲生,嚎啕大哭,刚刚经历千难万险才得以团聚的兄妹就这样阴阳两隔了。第二天,外婆掏出身上所有的钱,让母亲想办法去买两口棺材装殓表兄表嫂。因被炸死了很多人,大凡有点能力的人家都会按着中国的传统,不让冤死的亲人做野鬼,会想方设法买口棺材的,所以城里的棺材一时成了紧俏货。母亲费了好大劲才买到两口很普通很普通的棺材。我的大表舅公和大表舅婆就永远的躺在崇安城外的荒地里了。 太婆之殇 安葬了亲人,外婆完全一贫如洗了,不知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更不知再往何处去。但外婆毕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她老人家把无限的悲痛埋在心里,她不能让年迈的太婆过于伤心,不能让家人没了主心骨。一家人天天躲避着空袭,还得想法子糊口,母亲就到处找活干,今天帮这家洗衣服,明天帮那家缝被褥,好不容易赚到一点点钱,外婆就拿去买来白面,做成馒头摆在路边叫卖。 一天,母亲终于遇到一个在上饶认识的熟人,叫陈平,他正在替三战区开车运送撤退的物资。当他知道母亲一家的不幸遭遇后,便力邀母亲一家乘他的汽车一起离开崇安,躲到山沟沟里去。 逃难的人,四海皆为家。陈平把母亲和家人带到永安附近的小陶镇。原来小陶镇除几十户人家外,两边都是大山,极易隐蔽,三战区就把汽车藏在这山里。 太婆经受了这些日子的颠沛流离,特别是大表舅公和大表舅婆的死给她的打击太大了。老人家虚弱的身子已经承受不起更多的摧残和折腾,她病倒了。于是,一家人只好先住下。在镇外一公里的地方找到一个独户农家,有山有水,非常清净,如果不是战乱,绝对是个休闲养生的好地方。可是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山河失去了美丽的容颜,担惊受怕的人们哪有心思去观赏美景呐?三战区车队的人成天忙忙碌碌,随军家属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出车的丈夫回不来。外婆和母亲整日里守着太婆,希望她能好起来,捱到再次与我外公团聚的日子。太婆没有挺过来,终究还是病死在那个偏僻的小镇上,那时太婆还不到六十岁。在汽车队朋友们的帮忙下,她老人家被安葬在农家院对面的山坡上。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七十年了,但读母亲的回忆录,那战火纷飞,百姓惊恐的场面好像就在眼前。我理解了母亲为何把“9.18”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要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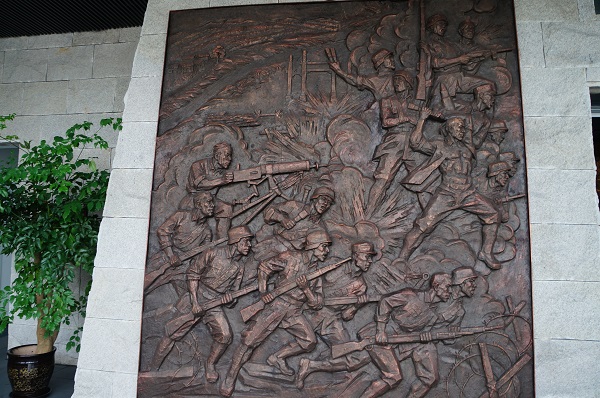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