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现在看来,那些被指认抄袭的段落,更像从别人文章里剪下来的碎布,拼凑起来的袍子,连针脚都透着潦草。这事儿像块石头扔进水塘,荡开的涟漪里,藏着五个绕不开的问题。 一问抄袭者:抄来的文字,能算自己的吗? 有读者比对过,胡竹峰某篇散文里写“春茶在杯中舒展”,和另一位作家十年前的句子“茶叶在沸水里慢慢翻身”,连动词的选用都如出一辙。更刺眼的是,他描述故乡的段落,几乎照搬了某本地方志的民俗描写,只是把“李家庄”改成了“胡村”。 写字的人都知道,每个词的选择都藏着心思。写“月亮”还是“月色”,用“走”还是“踱”,背后是作者独有的观察和感受。抄袭者就像偷了别人的钥匙,打开了本不属于自己的房间,却以为换把锁就能变成主人。胡竹峰在文章里谈“原创的尊严”,可当这些文字被扒出是抄来的,那句“尊严”听着像句笑话。 有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可抄和借鉴从来不是一回事。汪曾祺写高邮鸭蛋,脱胎于故乡记忆;鲁迅写“人血馒头”,扎根于现实观察。他们的文字带着个人印记,就像指纹,别人仿不来。而抄袭者的文字,更像复印纸,再清晰也没有自己的纹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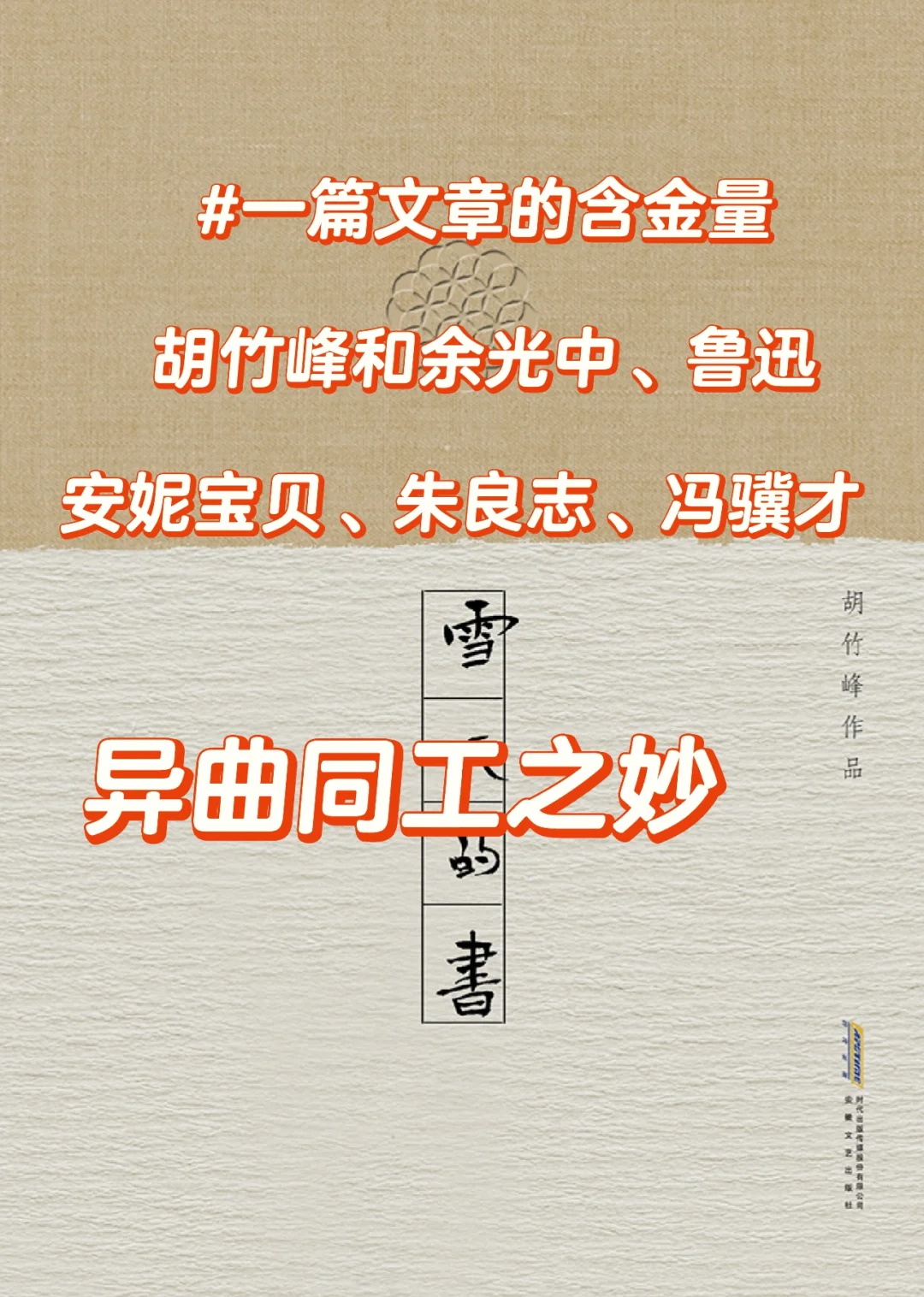 二问出版界:审稿时,眼睛在看什么? 胡竹峰的涉嫌抄袭文章,发过不少大刊,甚至收入文集。有编辑辩解说:“稿子太多,哪能篇篇都核对出处?”可读者随便一搜就能找到的雷同段落,专业编辑真的看不出来? 这里的猫腻,或许比想象中复杂。某文学杂志主编私下说:“名家的稿子,审稿时会松点。”胡竹峰这些年积累了名气,头上顶着“新锐散文家”的标签,稿子来的时候,编辑可能连校对都省了,直接按“免检产品”处理。这种“名气滤镜”,成了抄袭的保护伞——反正读者信名家,编辑也懒得较真。 更让人无奈的是“圈子效应”。文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彼此都认识。某篇涉嫌抄袭的文章,据说终审编辑是作者的朋友,审稿意见写着“文笔老到,推荐发表”。这种“人情稿”的潜规则,让抄袭的文字有了可乘之机,就像门卫看到熟人脸,连通行证都不查。 三问读者:我们对抄袭的宽容,是不是太廉价? 胡竹峰的读者里,有人说“只要文章好看就行,管它从哪来的”。这种心态像给抄袭者递了把刀,让他们觉得“抄了也没事”。 可文字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好看”。我们读文章,读的不只是故事,还有作者的真诚。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会被他对命运的思考打动;读萧红的《呼兰河传》,能感受到她对故乡的眷恋。这些文字的力量,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和独立思考。而抄袭的文章,就像假花,再鲜艳也没有花香,更结不出果实。 有个细节很扎心:被抄袭的那位老作家,已经八十多岁,还在手写稿子,说“每个字都要对得起自己”。可他的文字被抄走,读者却在为抄袭者叫好,这像在告诉认真写作的人:“你守规矩,就输了。” 四问文坛:为什么总有人铤而走险? 胡竹峰不是第一个被指抄袭的作家。这些年,从网络小说到学术论文,抄袭事件层出不穷。究其根本,是“出名要趁早”的焦虑在作祟。 现在写文章,想出头太难了。新人要熬很多年,可能才换来一次发表机会。而抄袭者走了“捷径”:把别人的心血改成自己的名字,迅速积累名气,拿稿费,评奖项。就像考试作弊的学生,用小聪明骗过了老师,还嘲笑认真答题的同学“太傻”。 文坛的评价体系也有问题。看一个作家好不好,往往先看发表过多少大刊,得过什么奖,很少有人追问“这些作品到底有多少原创性”。这种“数量优先”的导向,让一些人觉得“抄得巧”比“写得好”更重要。 五问写作本身:原创的路,还能走通吗? 记得,有个被抄袭的作家接受采访时,红着眼圈说:“以后不想写了,写了也是给别人抄的。”这话让人心里一沉。如果认真写作的人总被伤害,谁还愿意沉下心来创作? 其实,原创的路从来不好走。汪曾祺写《受戒》,改了十几次;莫言写《红高粱家族》,在部队宿舍里熬了无数通宵。但他们走得踏实,因为每个字都属于自己。就像老农种庄稼,虽然辛苦,但看着禾苗长高,心里是甜的。 胡竹峰事件该成为一面镜子。对抄袭者来说,该明白文字的债迟早要还;对出版界来说,该守住审稿的底线;对读者来说,该珍惜原创的价值。毕竟,我们爱的从来不是“好看的文字”,而是文字背后那个真诚的灵魂。 写作终究是件笨事,要慢慢来,要亲手写。就像种一棵树,从播种到结果,得经历风雨。抄来的文字,再光鲜也长不成大树,最多是朵塑料花,看着热闹,却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希望胡竹峰之后,少一些“捷径”,多一些“笨功夫”。让每个认真写字的人都相信:原创的路,虽然难走,但走得值。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