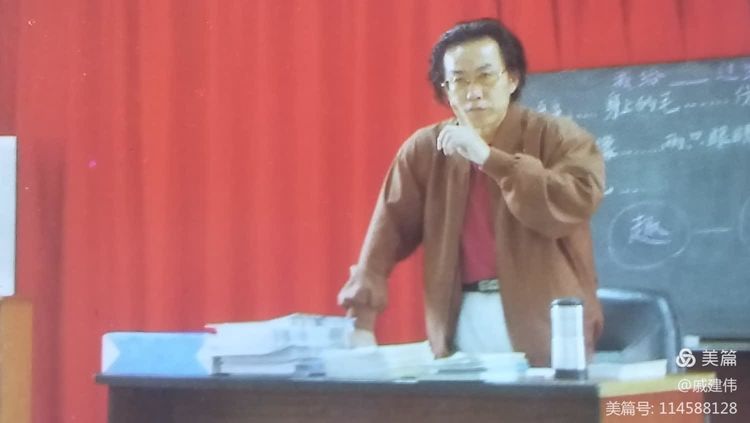我曾是一名藏区插队知青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吴长生 时间:2025-09-02 点击: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们也决心积极响应伟大召唤,到西藏农村安家落户。我们请求自治区领导安排我们到农村去搞一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拉萨东郊的一个村子。
虽然与测绘大队只隔几十里,但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吃的是酥油茶、糌粑面,住的是老乡土藏房,干的是起羊圈、背粪肥、背石块等农活,听的是藏汉交杂语。
第二年春天,我们又被派到测绘大队的农场去春耕,再次近距离观察农村、农牧民的生活。一次偶然的遭遇,给大家强烈的震撼。一天休息,大家决定到附近的一处温泉去洗澡。温泉在半山坡上,兴致勃勃的我们争先恐后地往上爬。贾小黎、郑友增冲在最前面。可刚爬上去一两分钟,他们就折回往下跑了,还拦住女生们,不让她们上去。怎么啦?“露天的,男男女女都在一个池子里!”啊?!大家惊呆了,不知怎么办。带队的战士找来当地基层干部,说明情况后,那位藏族干部决定把泡澡的老乡“请”出去,换新水供“北京客人”洗。我们一不同意赶走老百姓,二对男女共浴不以为然。得知来洗温泉的都是各种病的患者,我们就更不敢洗了。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两次与西藏农村的“零距离”接触,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能生存吗?你有毅力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吗?你能闻惯浓重的牛羊肉膻气加汗味儿吗?完全以糌粑、酥油为食,你受得了吗?“男女混浴”的习俗你接受吗?短暂的忍耐可以,而你能坚持多久?几个月,几年,还是一辈子?……面对这些问号,谁也无法回避。而恰恰也是在这段时间,东北边陲传来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消息,让我们很自然地又与自身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联系到一起,引发了进一步的遐想。没来西藏,想进藏;进了西藏,去何处?
大约是1969年6月初,拉萨已经进入夏季。不甘寂寞的同伴又酝酿着新的动作。一次我在整理铺位时,一位同伴神秘地提醒我“小心”。怎么了?他竟从箱子的缝隙中掏出了两枚铸铁水管做的土造手榴弹!哪来的?记不清了。干嘛用?留着过几天到拉萨河炸鱼去。我忧心地说,哪能放在这儿呢!但大家都埋怨我多虑。我只好沉默。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在家的所有男生,除了我,都要去炸鱼。看拦不住,我就叮嘱说:“千万留神,可别没炸到鱼,却把人炸了。”在连连的“没事”中,他们顶着烈日出发了。也就一个多小时吧,郑永安突然急匆匆地跑了回来,大声说:“不好啦,出事了,郑友增被炸伤了!”看着她土灰的脸色,我如五雷轰顶,急忙跟着她往前面跑,还没赶到卫生室,就看见一辆吉普车绝尘而去。友增被紧急送往总医院抢救了,与他一同受伤的还有李一伦,但他的伤不重,只额头擦破了点皮,友增则被弹片打穿了大腿。他是被刚一出手就提早爆炸的手榴弹炸伤的。
几天后,我到总医院探望已经做完取弹片手术的友增,又心痛又愧疚,因为四中的几位同学都是“跟着”我来的,特别是友增,我们是“发小”,从小学一直同学到中学。今他遭此大难,我怎能心安?!
几天后,因西藏不具备进一步治疗的条件,总医院建议友增回北京医治。很快,友增就被送回北京了。后来知道,友增的左腿坐骨神经被几乎炸断,别说西藏,就是全国也没几个人能治。通常的办法就是截肢。而友增还算幸运,协和医院的冯传宜教授(神经外科)、乐铜教授(外科)给他做了手术。他们都是国内这方面的最高权威。
由于友增被炸,测绘大队领导强烈要求把我们这帮“捣蛋”的北京中学生转走。1969年7月中,我们就告别了藏字512部队,转到了拉萨河南岸的军区政治部农场,与早期到这里的那拨北京学生“会师”。
在政治部农场,有同学夜晚蒙在被窝里“偷听敌台”,从美国之音广播中得知了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的消息。当他把这一消息在黑暗中低声告诉大家时,似乎并没有引起特别的“热烈”反应。彼时的我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到哪去”,人类第一次在月球表面留下脚印的重大科学突破,实在离我们过于遥远,更何况那还是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事。
半年多的“悬空”状态,使我们的思想开始分化:在军营却不是真兵,少部分人萌生了“转正”,入伍当真兵的想法;大部分“出身”不够格的同学不敢动这方面的念头,进机关也根本别想;西藏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企业,务工的机会微乎其微。剩下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到军区生产部下属的农场去当农工,二是直接到农牧区公社插队。但两次与西藏农村的“零距离”接触,又使多数原来打算插队的人发生了动摇。
在插队问题上,我坚定不移,认为这是落实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实际行动,也是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我一直把保尔当成偶像,此时就从心里把不愿下乡的同学们都当成了“冬妮娅”那样的“同路人”,有意疏远了。一起进藏的十几个人,只剩下3人坚持要插队,但我认为我们是“光荣的少数”,是“革命的孤立”。
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十二三岁争取入团起,就不断检讨与生俱来的“家庭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刻苦改造世界观,“自觉到最基层、最艰苦”的环境中去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几乎已成为我的一种“本能”。背后无大树、头顶没余荫,也“逼”出了我不依靠别人的坚韧性格。依然与我一样坚持要求下乡插队的胡绎、刘晓莉,被我视为志同道合的坚定战友,我决心与他们一道尽快奔赴农村,迎接新的战斗洗礼。
1969年8月初,我们告别政治部农场,奔赴山南地区农村。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这是在西藏插队与内地下乡最大的差别。刚到东来时,我们与老乡沟通很困难。好在东来队就在县机关所在地,因此不少年轻人多多少少都会说一些汉语,而多数人能听懂日常用的汉语。我们就一句一句地向老乡们学藏话。两三个月后,“汉话、藏话加比画”,成为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而随着时间的延续,汉话、比画越来越少,藏话越来越多,大约不到一年,我们就完全“藏化”,不仅可以与老乡们毫无障碍地交流,而且能附和着说“荤笑话”。
插队那3年,正处于极左思潮风行的年代,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的我们也干了不少荒唐事。其中一次“拦路”打劫,就让我终生愧疚。
大约是1970年秋天,按照上级部署,加查农村开展了反对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运动。除了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学习会上做忏悔式的自我批判外,以高度的警惕性观察身边的“阶级斗争新苗头”,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新动向,也是衡量革命觉悟高低的一个基本标准。为了紧跟形势,我们也挖空心思,寻觅蛛丝马迹,创造斗争机会。这时有人提出,东来公社的西邻藏木公社有人自己烧制茶壶、水罐等,私运到洛林区去交换酥油等畜产品或直接出售,用以补充衣食不足。
藏木公社是加查的陶器产地,素有烧陶的传统,但公社、生产队都坚持以粮为纲,不搞这种偏离主业的副业,制陶全是社外的单干户或社员业余时间的“私活”。制陶本身并没被划入“非法”,因为产品主要卖给本地乡亲或区供销社。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自行运到外地卖,就被视为“投机倒把”了。这里有两条“线”:一、公社加工厂生产的东西,无论卖给谁,都姓“社”;二、个体生产的东西,只要在本地卖或卖给“公家”,就不姓“资”,但把个体生产的陶器私自运往另外一个区去卖,就“犯法”了。
从藏木到洛林,洛林沟石桥是必经之路,而这座桥就在加工厂大门外。每天有什么人、带着什么东西从桥上过,我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堵住这条“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黑路,我们决定在桥头设“哨”,一旦发现“情况”,即行查扣。
没想到设“哨”的当天,就取得了“战果”。上午10点左右,负责“瞭望”的小伙子报告说,一个背着满满一筐陶器的人正从藏木方向走来,还赶着一头驮着陶器的毛驴。我们闻讯立即兴奋起来,如临大敌,赶到桥头准备阻拦。那人全然不知地朝石桥走来,根本想不到已经劫难临头。刚刚走过石桥,他就被我们拦下,看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他发觉不妙,脸色顿时变得煞白。结结巴巴地回答了询问之后,我们厉声指出了他“投机倒把”行为的严重性质。得知他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后,我们更提高了批判的嗓门。桑木冬队的社员也闻讯陆续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加入了批判的行列。桥头举行了一场“人赃俱获”的小型批判会,那位藏木的老乡一直哈着腰,频频点头表示“认罪”。由于“态度好”,我们决定“宽大处理”,只没收陶器,不没收“投机倒把的重要工具”——毛驴,放他回家,并让他警告那些与他同样有“投机倒把”念头的人,不要重走邪路,否则会更加严厉惩处。那位老乡灰溜溜地返回了,多天的心血化为乌有。而我们则在桥头摆开了“卖场”,把所有陶器低价卖给了围观的众位乡亲,赢得了一片赞许。卖陶所得的30多元,全部上缴集体。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换粮食,能换两三百斤呢。
从内心讲,我当时其实很同情那位藏木老乡,看着他垂头丧气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但受大潮流推动、大气候感染,我难以自已,常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而干类似的荒唐事。我们的这次打击“投机倒把”行动,其实无异于拦路抢劫,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它不仅伤害了那位藏木老乡,而且造成恶劣的影响,封堵了无数农民依靠自己力量弥补衣食不足的路子。
我们插队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与内地不同,西藏、新疆、内蒙古三个民族自治区的运动,夹杂了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就在我们争取下乡的过程中,1969年,西藏尼木等少数县发生了被定性为武装叛乱的暴力事件。
大规模的“整肃”运动大约是从1971年秋天开始的。这之前不久,西藏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西藏军区司令员、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曾雍雅被调离西藏,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西藏军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R某,接替曾担任革委会主任,成为自治区“一把手”。
1971年8月,西藏举行第一次党代会,R某当选第一书记。当时在西藏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曾雍雅调离的主要原因就是“平叛”、清查不力。而以派性明显、支持“大联指”著称的R某主政伊始,便雷厉风行,迅速把整肃“暴乱”“复叛”“预叛”的风暴,燃向全藏,与“一打三反”结合在一起。
东来公社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发动群众,动员大家放手揭发有关“预谋叛乱”问题。凡是对解放军不满的言论、行动,都在清查之列。
在工作队的鼓动下,全公社掀起了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的“揭批”热潮,一些原来的“闲人”活跃起来,也精神起来。围绕着我们,各种传言纷纷而来:“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为什么不在北京待着,到西藏边疆来干什么?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要那么多波段的高级收音机干什么,可能是用来与境外特务组织联系的。”……西藏偏远,加查更偏远,在执行“最高指示”中的“创新”,就更加偏激。作为知青中的“出头椽子”,我先是被工作队负责人G叫去,接受“政策教育”的训话;没过多久,又被“请进”学习班,晚上不准回家,也不许与外人交谈,大概是“防止串供”。工作队还重点清查了我所负责的公社加工厂的账目,可翻来覆去地查,最后是“分毫不差”,只能作罢。但由于我的原因,加工厂被解散了,所有人返回各自原来的生产队,我则回了东来队。隔离“办班”“背对背揭发”,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疏离了我与一般社员的关系。为了“少惹麻烦”,大家减少了往来,平时接触也不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了。
我们发现运动开展以后,连家信也“走”得越来越慢了,从以往的一个半月延长到两三个月,更惊人的是,收到的家信竟然有被拆开的痕迹。报纸“迟到”,私信被查,广播信号微弱不稳,我们基本与世隔绝,成为“信息孤岛”上的现代“鲁滨逊”。
大约1972年初,对“复叛”问题的清查在拖延了几个月后,终于收场,好像也没做什么结论。但运动依然要“紧密结合本地的阶级斗争实际”,把原本已经被专政的仲巴代理人等老四类分子拎到前台,硬逼着他们承认“一直妄图复辟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时时刻刻想着变天”。我曾参加过几次这种批斗会,夜晚,批斗会以篝火堆为中心展开,批斗对象被安排在临近火堆的地方弯腰站着。围坐的社员不时发出质问、批判。情绪激动时,有人便站起来边高声责骂、边推搡,把“主角”故意往火堆方向推。好几次,仲巴代理人险些被火苗燎到头发,脸庞被灼烤得通红。躬身站在一旁的“陪斗”家人,被吓得瑟瑟发抖。批斗之后,队里还安排几个年轻人悄悄爬上仲巴代理人家的房顶,从火塘上方的出烟天窗偷听屋里的对话,看有没有“不满的反动言论”,为下一轮批斗准备“炮弹”,但没取得任何成果,只听到仲巴代理人痛苦的呻吟声。
在我的记忆中,总共一百来户的东来公社,至少有五户变成了新的“专政对象”。二十多户的东来村,就有两户原来的富裕中农被“升”为富裕农奴(即内地的富农),而这两户恰恰都是我们的邻居。仅一墙之隔的近邻,就是那个被排斥在公社外面的单干户,家里劳动力较多,还有几头大牲畜,地也比较好。隔几户的那家,男的是有手艺的木匠,被定为富裕中农,但因老婆的成分是奴隶,他们被吸收进入了公社。成分一“升级”,立马由“友”变“敌”,那个近邻被“扫地出门”:原来的房子,分配给了队里的两个贫困户,他们全家被驱赶到村边的废屋中暂时栖身,随身只带了简单的个人生活物品和简陋的农具,藏毯、马鞍、藏柜等“奢侈”物品统统被没收。不久后队里搞了“浮财”的折价拍卖,但只有贫下中农拥有购买权,一般是用很低的价格买到“称心”的东西。原来富裕中农成分的木匠本人升级为富农,成为打击对象。
东来公社的其他队有没有“阶级成分升级”的记不清楚了,但在“一打”中被新划成反革命分子的,至少还有三人。他们有的曾经在寺庙中担任过低级职务,有的从事过“跳神”一类的活动,除了“清算”历史老账,还被揭发出诸如“诅咒共产党领导”“对公社化不满,埋怨干活累、吃不饱”等“现行反动言论”。其中一位还是公社革委会委员。由于不愿接受一下变成敌人的现实、忍受不了轮番批斗,三人中的两人“外逃”了。为了防止他们“叛国投敌”,公社组织了几路人马分头追捕。几天后,在雅鲁藏布江上游、朝桑日县方向的一个江边岩洞中发现了其中一人的尸体,本来已经年迈的他,是过度疲劳、惊吓、冻饿而死的。
经过和平解放、平叛改革、公社化、“文革”,西藏的阶级敌人队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扩充、日益增强,这真令人啼笑皆非。
作者简介:
吴长生,1968年到西藏参加边疆建设,1972年进西藏日报社工作,是进入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藏北“无人区”采访的第一个新闻记者。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83年进《人民日报》工作,先后任经济部农村组组长、经济部副主任、华东分社常务副社长、总编辑、香港办事处主任兼首席记者、国际部主任。
(责任编辑:林嗣丰)
(责任编辑 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