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连载十一)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夏建丰 时间:2025-08-04 点击:
遇险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几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对于我来说,迄今为止遇到的最为危险而且自己认为有可能危及性命的事情,都发生在我做农民的时期,发生在里陂上村。
一、红毛豺狗(豺)
在里陂上的时候,白天要出工,理论上的工作时间是一天十小时:早上二小时,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十小时以外的其他一切琐事中,砍柴和种菜是最重要且费时费力的两件事之一,没有柴不能做饭。没有菜的后果当然是只能吃白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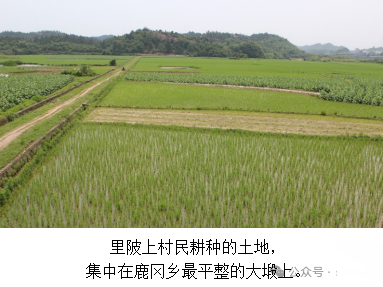
好不容易等到队长一声吆喝:“收工!去归!”我就像兔子一样窜出去(子庸看见过我在上海着急过马路,等绿灯一亮时就这样窜过),一路疾走到了北坑。在里陂上村,跑叫走,走叫行,古今不变。
刚进北坑口,我正沿着旁边谷底的小路疾走,听见右面的山梁上的灌木丛里一阵哗哗的响动。奇怪,莫不成有人收工以后,上山砍柴比我走得还快?不大可能啊。难道是哪个不出工的老人下午在山上砍柴还没有回去?我边走边想。
在山里走小路,必须看着前面十步左右,高抬腿,迈小步,不容人随便左右张望,否则很容易一脚踩空,滚下坡去。可是右面树丛里的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眼珠不由向右侧瞟去。
真真的是说时迟那时快,眼角闪过一道橙红色的闪光。我立马停住,瞪大了眼睛。前方十米不到,约莫在齐人高的空中,有一只橙红色的比狗大一点的动物,身体水平伸长,前腿和后腿与身体成一直线,头部颈部和前腿平行。我身后的夕阳照过去,那橙红色的动物和远一点的浅绿、深绿、黄褐色的树丛一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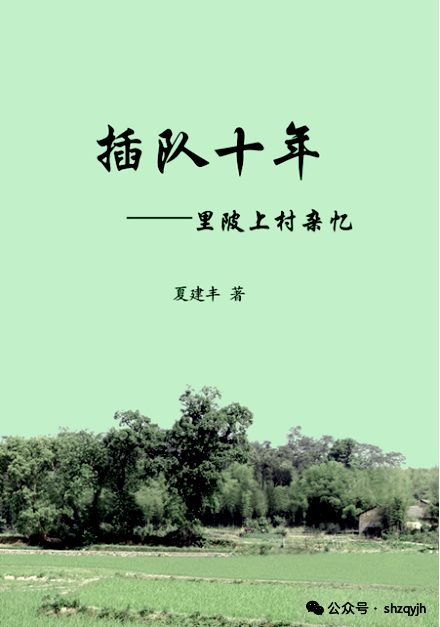
那只红毛豺狗缓慢地从空中落下来,前腿在谷底的路边轻轻一点,像闪电一样,又是漂亮的一纵,足有六七米远,落在左前方的山坡上,回头看着我。
不容我多想,哗的一声,树丛开处,右前方七八米处又窜出一只红毛豺狗,也是那么一跃一纵,瞬间就到了第一只红毛豺狗身边,哗哗地钻进树丛。
天哪,动物的速度哪是人类可以比拟!如果它们刚才是跳起来咬我,那么我的柴刀还没举起,喉管肯定已经被咬断了,肚子也扒开了。我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柴刀,还好,刀口是向外的,如果豺狗扑上来,兴许还能抵挡一下。我本能地想举起柴刀,不料两臂却是僵硬的,柴刀怎么也举不起来。不过我的脑子还在转。哦,刚才那第一只红毛豺狗回头看过来,其实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我右前方的它的同伴。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突然听到了野兽的叫声,有点像狗叫,声音比大狗的叫声要细一点尖一点,比小狗的叫声要响一点。
我循着叫声看过去,左前方的山腰上,那两只红毛豺狗露出上半身,正在对着我叫。它们在打我的主意,它们要来了!我想往后退几步,可是我一步也不会动,脚发软,身体要往下瘫,更要命的是想要小便。只是我僵住的双手依然紧紧握着柴刀。
身后右边的树丛哗哗作响,我不敢往后看,僵硬的脖子也无法转动。
从我身后五六米的地方窜出来另外两只红毛豺狗,它们一前一后,开始嗷嗷地叫着,向对面山腰上等待着它们的同伴跳跃而去,很快隐没在树丛中。我眼看着对面的树丛一边晃动着一路向上,一边哗哗作响。倏忽间,山野归于一片寂静。我知道,它们已经翻过山梁,远去了
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要是我的腿刚才还能听话,真的后退几步,就和红毛豺狗狭路相逢了……
四周再没有什么可疑的声音,我就这样坐着。
不知过了多久,低头发现手里拿着柴刀,想起我是来砍柴的。挥动一下手臂,站起身来抬头一望,还有一抹落日的余晖。
砍还是不砍?这是一个问题。像平日那样到远处去砍柴是不可能了。空手回去?我岂不惹人笑话了。我四处张望一下,不远处有棵不大的松树,那按规定是不准砍的。可巧它的树干在二人高处分成了二股,一股大一股小,小的砍下来估摸着会有四五十斤重。树枝没有明令不准砍。算了,就是它了,凑个数吧。
我把柴刀插进背后腰上的皮带,三下两下上了树,开始砍那小腿般粗细的树枝。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有些恍神。就在砍到最后几下的时候,我手一软,刀口滑到脚背上,出血了。几乎与此同时,树枝嘎嘎作响,掉在了地上。我连忙下树,天色昏暗中我胡乱扯了一点松针,嘴里嚼烂后敷在脚背的伤口上,扛起树枝,一瘸一拐地摸黑下山。
回到住处,点起油灯一看,脚背的伤口虽然不大,却伤到了静脉。我赶快用井水清洗伤口,再咬着牙用酒精擦拭,涂上红药水,撒上消炎粉,最后用纱布包扎好。
第二天全队的工作仍然是耘禾。我的脚伤了,怎么下水田呢?
我想起以前在书上看到过,正规军的战士们如果要背着枪泅渡过河,往往会在枪管口内涂上一段凡士林膏,以防止枪管进水。
我马上从箱子里翻出从上海带来的凡士林膏,在我脚背的伤口上涂了厚厚的一层,再重新包扎好,就下田耘禾了。村民们见了,都问我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遇到了红毛豺狗,我怎么会脚上包着纱布下水田呢?
如果不是遇到了红毛豺狗,我怎么会亲身体会到“吓得屁滚尿流”,几乎要尿流呢?
如果不是遇到了红毛豺狗,我的右脚背怎么会至今还有一个疤痕,右脚的中趾又怎么会缩短了一点呢?
记得1980年代,一个中国作家遭遇车祸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说是汽车翻转的时候,他觉得比电影里的慢镜头还要慢。那第一只红毛豺狗在我面前的跳跃,也是那么缓慢,却又那么优雅。
据说,红毛豺狗最喜欢吃动物的内脏。它们围攻耕牛时,牛会低下头来左冲右突,和它们搏斗。而那只本领最大的红毛豺狗往往抓住机会,突然跳上牛背,低下头去,咬破牛尾巴下面柔软的后腹部。耕牛受不了,忍痛狂奔,红毛豺狗紧追其后,直至耕牛肚裂气绝,倒地而死。红毛豺狗们一拥而上,吃光了牛的内脏,然后扬长而去。
又据说,红毛豺狗和北方的狼一样,是成群活动,连王八老虎(华南虎)都打不赢红毛豺狗,就不用说豹虎仔(金钱豹)和野猪了。我遇到了红毛豺狗,应该谢谢它们的不吃之恩。
我遭遇红毛豺狗之前,已经和它们有过间接的接触和了解,那是在一年前的一天。
那天我们正在鹿冈公社参加唯一的一次全体知青大会。老队长张发茂笑眯眯地到会场,找到了我们。他说,刚才他拿着一只野猪脚到公社,公社按照政策,奖励了他十六元。
什么?野猪脚?
原来那天中午,发茂砍柴回家,挑着柴经过里陂上村北面的小水库的坝顶,此时水库里的水基本放完,他突然发现水库内裸露的山坡上,有一群红毛豺狗正在围攻一头野猪。发茂便在坝顶,远远地大喝了几声,然后赶快回家,拿了打猎的铳,约了两个人带着禾担和麻绳一起返回水库。
此时红毛豺狗已然散去,只剩那头开膛破肚的野猪静静地躺着,内脏已被洗劫一空。发茂他们几个人把没有内脏的野猪抬回村里一称,有二百二十多斤。

其实,公社的那十六元钱应该奖励给那群红毛豺狗,是它们杀死了那头野猪。发茂沾了红毛豺狗的光,得了一个大便宜,连带着我们也沾光吃到了野猪肉。
二、摔了个倒栽葱
里陂上村的男人过了五十岁,许多人就会剃成光头。可是张茂仁不到五十岁,每次剃头师傅来村里,他就要求剃光头,头皮青亮青亮的。他说话有些结巴,我们叫他“结巴子”,他会爽快地应承。若是叫他“野猪咬的”,他便面有愠色。
茂仁走路有些摇晃,上身摆动较大。他之所以走路摇晃,乃野猪所为。他年轻时参加围猎野猪,持铳守伏在暗处。不意一头成年野猪受了惊,朝他直奔而来。茂仁屏气扣动扳机,那野猪已然中弹,却未击中要害,反而加速冲向茂仁。茂仁手上的铳还没来得及装上第二发打野猪的独子铁弹。他一看大事不妙,只能落荒而逃。野猪追上来,在他屁股上咬了一口,然后突出包围,消失无踪,只留下茂仁在那里撕心裂肺地喊叫。茂仁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从此以后走路摇晃。
茂仁夫妇和五个孩子挤住在破旧的老屋里,很想再造个新屋,可是按照规定,造新屋不许占用耕地。无奈之下,张茂仁想在紧挨着他老屋后面的屋背岭脚下,挖出一块屋基来。屋背岭是里陂上的来龙岭,事关里陂上村的运气,谁也不赞成茂仁的想法。
茂仁来找我。我虽然不相信屋背岭和里陂上村的运气有什么关联,但是这么棘手的事情我也很为难。我只有把矛盾上交,和茂仁一起去找大队书记,请大队来决定。结果大队批准了张茂仁造新屋,我自然也因此得罪了一批村民。
于是茂仁每天天不亮,赶在出早工之前,他带领儿女们在屋背岭劈山挖地基。茂仁的新地基离我的住处不远,那镢铢挖土时发出沉闷的吭吭声,时常会扰乱我的梦境。这是那个时代的施工噪音。
半年以后,茂仁这位当代新愚公,终于率领着儿女们在红土的屋背岭开出一块三开间的新地基。
离新地基不远的屋背岭上,有一棵二人才能合抱的大樟树,它有一根直径将近二尺的枝桍,正好伸到茂仁的新地基上空。要是他的新屋造好了,万一有樟树的树枝掉下来砸在屋顶上,会出大事的。
茂仁又来找我,要我帮他砍掉这大枝桍:“老夏,你会上树,帮我砍了它,给、给你换工分。”

“我找了,冇人肯帮我。树桍下面造不了新屋,你、你好人做到底吧。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就依你吧,不过砍下的樟树桍要归我。”
“制得(行/可以/同意)。”
要砍的大樟树的枝桍离地有五米左右。我在树下先把两架三米长的杉木楼梯用麻绳绑在一起加长,把砍树的斧头用二米长的麻绳吊在楼梯头上,然后慢慢竖起楼梯,靠在大樟树上。我爬上楼梯,拉起吊着的斧头用力一甩,斧头绕过了树桍。我再登上几格楼梯,左手指用力勾住大樟树皮上的缝隙,右手够住那树桍,贴身靠住樟树,手脚一用力,纵身上去了。
我左手扶住樟树,站在树桍上,里陂上村那些黑黢黢的屋顶就在脚下。不远处有些人已经在田里开始干活,还有些人掮着镢头在田塍上慢吞吞地走。远处一直可以看到南满贯山脚下,鹿冈公社著名的里陂上的圆塅尽收眼底。
我就近估量着,这大树桍的直径约有二尺,用斧头开的口子至少要有八寸宽,才能最终砍断它。口子的左边离开树干应该有一尺,好容我左脚站立,右脚要站在口子的右面。我想,砍到最后时,依照经验,树桍应该会发出轻微的爆裂声。那时我必须迅速抽回右脚,站到左脚所在的那一尺地方,双手要紧紧抠住樟树,等待那树桍折断时几秒钟的嘎啦啦爆裂声和轰隆隆倒地声。最后再小心地沿着楼梯慢慢下树。
我弯腰拉起麻绳拴着的那把斧头,小心站稳,开始工作了。咚咚的砍树声可以传出很远。(有时看见一个人在远处砍树,斧头砍下去没声音,斧头举起来才听见咚的一声,很奇怪很好玩。斧头从砍到树再举起来大约一秒钟,所以此人应该距离我们三百多米。)
我双手执斧,砍一阵要歇一下。抬起头来,我可以看见田里干活的人。有人撑着镢头把,在朝我这边看,还有些人对着我这边指指点点。他们一定听到了咚咚的伐木声,都知道了我正在砍断来龙岭上樟树的枝桍。他们一定在议论纷纷,可惜隔得太远,我听不见。
过了约一个半小时,我终于听到树桍发出了轻微的爆裂声。我赶紧缩回右脚,紧紧贴住树干。没有动静。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奇怪。
我沿着树干慢慢蹲下,左手扶住树干,右手单手执斧,试着继续砍。
单手执斧的力量太小,还是没有动静。
我站起来,身体的重心尽量往左边靠,右脚轻轻点住口子的右侧,斜着身子,双手执斧砍了起来。
刚砍了四五下,我只觉得身体一晃,右脚本能地往左边一缩。来不及了。嘎啦啦啦,大树桍往下沉,我手中的斧头脱手飞了出去,双手胡乱在空中挥了三四下,想抓住点什么东西,当然什么也没抓住。
我的头朝下,眼睛看着大树桍,随着它的轰隆声,我和大树桍几乎是同时落到了地面。我的双手挥舞着,摔了一个倒栽葱。
我翻身坐起来,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大树桍。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周身上下没有异常反应,没事。
村民周恩绍从干活的田里一路冲上山来,着急地叫道:“老夏,老夏!”
我跟随着老周的目光,看见右面地上松软的腐殖质上,有一个大约二寸深的圆坑。我知道,那是我的头顶和地面亲密接触的结果。倒栽葱的结局还算圆满。
然而就在圆坑旁边一尺远,赫然有一个约四寸高的尖利竹桩,正在狰狞地看着我。我和老周都看到了。
老周大声叫起来:“哪……老夏,你好危险!……你命好大!”
“……屋背岭是里陂上的来龙岭,事关里陂上村的运气?! ……”想到这里,我的腿脚有些发软了。
我曾经在张贡茂家里搭伙,就把樟树的大树桍给了他。他第二天就请来木匠,打了一张吃饭用的方桌,那樟木桌面就是大树桍的一部分。
没过几天,心里不高兴的里陂上村民到大队告状成功,大队派人到张贡茂家,把余下的樟木树桍统统没收了。这些树桍堆在大队部,成了大队干部冬天烤火的材料。这着实让我心疼了一下。真可惜了这些让我头朝地倒栽葱的樟木。
冬天快过去了,有一天我路过大队部,看见一截最大的樟木树桍还没有烧完,就打趣说:“整个冬天你们用我的这些桍来烤火取暖,省了大队很多钱吧。”不想大队干部笑嘻嘻地说:“我们真是背时,用你的樟树桍烤火,樟油一烤出来,辣得我们连眼珠都睁不开,还直咳嗽,我们就像烟熏的蚊子一样。”
后来我到公社去,遇见了老是那么笑眯眯的公社管知青的知青办主任,他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夏建丰啊,听说你这次犯错误了。砍了樟树也不告诉我。你要是送给我该有多好,我可以做樟木箱啊,看谁还敢乱说话。”
贡茂在事后告诉我,当我在帮茂仁砍树时,在田里干活的姓张的村民群情汹汹,他就知道我闯祸了。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客居在里陂上村的外姓人周恩绍一个人冲上山来看望我的原因。有些姓张的村民真有可能希望我从樟树上掉下来呢。
贡茂说,他舍不得我送给他的樟木。他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已经知道村民们会联合起来,到大队去告我的状。他便抢在前面,迅速打了一张方桌。按理说大队来人应该没收那樟木的桌面。可是除了桌面,打桌子用的杉木都是贡茂很久以前自己花钱买来的。桌子已经打好了,大队来的人无法下手。
赢弱的驼背老人贡茂,他在村里老是受人欺负,却也能想出这一招,够聪明。
几十年以后,我在里陂上村张贡茂的儿子张绍生(水根仔)家里,发现那张樟木桌面的方桌还在使用,桌面上依然有两道宽宽的裂缝。那是贡茂当年没等樟木干透,就匆匆忙忙地赶工做方桌所留下的痕迹。
挨饿
自从看了电影《天下无贼》以后,我开始喜欢和关注这位导演的创作。2012年,他的新片《1942》讲的是大饥荒,正好我们这里的AMC院线的大股东是中国企业家,《1942》得以和中国的电影院同步上映,我一共看了三遍。我女儿苏舒看了两遍,她觉得《1942》是这位导演拍得最好的电影,比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还要好
在里陂上务农的日子里,我曾经试过只吃菜不吃饭,坚持了五天,知道忍饥挨饿的滋味真不好受。
我刚到里陂上村,就常常会听见年长的村民教训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的后生说:“唉,你们真是冇饿过饭啊!”
里陂上村现在耕种的田地,在解放以前多数属于李家村、袁家村和上头村里的财主人家。在一定程度上,里陂上可以说是一个长工村,多数人家给财主打长工。长工的收入要根据田里的收成来决定,一般是按四六分成,长工拿四成,财主人家拿六成。上交的农业税不重,由财主人家负责缴付。
长工之间有很自然的信息交流,他们知道谁家的田里收成好,谁家的田里收成差。他们也知道哪个财主刁钻吝啬,哪个财主宽厚大度(插秧割稻时会请长工喝酒吃肉)
1949年解放以后,土地改革划定成分,财主人家绝大多数定成了地主,他们的田地被没收,分给了穷人。里陂上村的二十几户人家,没有一户地主富农,中农也只有一二户,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
在解放以前,贫下中农的家里毕竟底子薄一些,没有陈年的积蓄,生活相对比较清苦,遇到年成不好,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会饿饭。
等到土地改革以后,里陂上的村民家家都有了足够的土地,就极少有挨饿的事情发生。
村里年轻的一代没有挨过饿。他们有时会出工不出力,偷一点懒,耍一点奸,一边混工分,一边还满不在乎。他们有时还会发一些牢骚,对上级领导的某些作风和态度表示不满。
每逢这种时候,从前饿过饭的年长的村民,就会发出“你们冇饿过饭”的感叹。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家境稍微宽裕一点,至少是衣食无虞。每当我感到肚子有点饿了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吃饭的饭点,记忆中从来不知道饿一顿饭是什么感受,“少年不识饿滋味”。
在我种田当农民的最后数年,里陂上村只剩下了我一个知青。这时候的我,各种农活都已娴熟,我在自留地里种的各种蔬菜也是郁郁葱葱、硕果累累,一个人根本吃不完,有时候会送菜给在其他村里插队的知青。
有一天,我又听见村民在训斥自己的孩子,还是那几句饿饭的老话。
我突发奇想:这些老人以前都饿过饭,不吃饭究竟是什么滋味?我现在有这么多蔬菜吃不完,如果我几天只吃菜不吃饭,会是什么感觉?
我决定自己来试试看。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的早饭,我炒很多青辣椒,中午则是两大碗蕹菜。
晚饭除了辣椒和蕹菜,还会吃一些茄子和瓠瓜。
我除了只吃菜不吃饭,其他的一切活动照常进行。我白天要下地干活,另外要挑水、砍柴、种自留地、烧饭和喂猪。晚上睡觉以前,我习惯看一点书。
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我的感觉正常,只是胃里面有一些泛酸,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到了第三天,我感觉有点不对了。挑一担水,装满水的水桶不容易控制,有点摇晃。在田里做事也比平时容易累,容易出汗。第四天收工以后去砍柴,发现手上力气变小了,柴就不那么听话。挑柴回家的路上,有点心慌、气喘。
到了第五天出工的时候,我挑了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来做。当我走在田塍上,只觉得心也慌,头也晕,脚下轻飘飘,身体摇摇晃晃。我突然打个趔趄,差点滑倒,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只想快点回家休息。
我平日的夜晚躺在床上,隔着蚊帐,就着蚊帐外面床边上的油灯看书,是一种享受。可是今天晚上不行,书上的字老是会滑走,老也抓不住。我已经五天只吃菜,没有吃米饭了。
第六天早上,我拿起圆镜照看自己的脸庞,发现脸色不但发黄、发灰,更是隐隐发绿,有点像没有施肥长得不好的蕹菜的颜色。我恍然大悟,知道“面如菜色”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了。
我放下镜子,赶快洗米、生火、煮饭。饭的香味出来了,我不停地咽口水。
真到吃饭的时候,我倒不觉得饭有多么香甜,只是吃得特别快特别多。
我在里陂上村做农民能够吃饱,这真是天大的幸运。
而相隔二里路外的潺陂村就不行,他们的人口和我们村相彷佛,田地却只有我们的一半左右。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潺陂的村民会走一百几十里路,到上永丰的藤田一带,悄悄地到农民家里买薯仔渣来充饥。
藤田地区盛产红薯,当地有名的土产是红薯淀粉和红薯粉丝,下脚料就是薯仔渣,主要用来喂猪。
有一次,村民张发茂从潺陂村的亲戚家带了一点薯仔渣回来,路上遇见我。
“老夏,要不要尝一下?”
“啥东西?”我问。
“薯仔渣。”
“吃一点。”我早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吃过薯仔渣。
我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小口,一股馊臭味直冲后脑。我强忍住恶心,咽了几次,薯仔渣直刷喉咙,终于咽下去了。
看见发茂正瞪大了眼睛在看我,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我知道,自己的脸上一定很难看。
“好吃吗?”发茂坏笑着问。
“怎么拿这种东西回来?”我摇着头问。
“女儿没吃过,听说有薯仔渣,想吃。”
“贵吗?”我问发茂。
“六块五一百斤。”
“一百斤稻谷才九块五。”我说。
“那是国家牌价的稻谷,私人要卖十九块,还不准卖,卖了要犯法。
再问下去,我才知道,藤田的农民秋天收了红薯,冬天做了薯粉以后,剩下的薯渣就堆放在那里,任其变味发酵。这样的薯渣到了春天,还能是什么味。六块五一百斤的薯仔渣,能有钱买,能买到吃,就不错了。
1980年代我去北京出差,大白天出去溜达,在西直门外见到很多人在排队买豆汁。我也凑热闹,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一碗。坐下一喝,却是薯仔渣的味道。我勉强喝了几小口,就把碗放在桌上,溜走了。凡是碗里的食物,我一般都要吃完,这次是例外。
我后来听说,豆汁是北方人用绿豆做粉丝后的下脚料发酵了做成的,怪不得和薯仔渣的味道差不多。
我在里陂上只吃菜不吃饭才五天,如果连菜也没有吃,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逃荒的灾民,我会放下那碗豆汁走人吗
我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上小学了,我就告诉他:“你要开始负责自己的早饭了,冰箱里有牛奶、面包、果酱和黄油。你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想饿肚子,那是你自己的事。”
儿子长大以后,有一次我问他:“肚子饿了没饭吃,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他马上回答:“知道。很难受。”
儿子告诉我,他上小学的时候,真的试过不吃早饭就去上学,结果在课堂上饿得头昏眼花,难受死了。从那以后,他坚持每天早上在冰箱里找东西吃,吃完以后再去上学。
听他说完,我笑了:“很好。这是你小时候得到的人生第一笔财富。”
儿子和他的姐姐一样,除了很注意不要浪费粮食以外,现在还会自己动手,烧出可口的饭菜。
有人在将近一百年前说过,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现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大多数人能吃饱,还时不时很浪费,嚷着营养过剩,嚷着要减肥,嚷着要养生。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周遭还是有人在忍饥受饿。况且谁也不能保证,今后我们这个世界不会发生大饥荒。
受冷和烤火
每到寒冷的冬天出工的时候,里陂上的村民常常会缩着脖子说:“老古话说的是:热是热众人,冷是冷个人。”
热是热众人。夏天的农村没有冰箱,没有空调,过去的财主人家和一般人家一样,你光着膀子,我也光着膀子,再没有衣服可以脱了,众人一起受热
冷是冷个人。到了冬天就各不相同了。过去的财主人家比较富裕,他们冬天出门可以穿皮袄,穿棉裤,戴皮帽,他们不下田干活,他们不会冷。至于一般的村民,上身可以有夹袄,有棉袄,可是他们冬天经常要出门干活,下身只有穿单裤才行。他们家里往往只有单裤,出门只能受冷。冬天冷到结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穿上两条甚至三条单裤来御寒。当然,如果是冬天农闲在家里,可以围在火塘边上烤火取暖。这时候就是只穿一条单裤也不觉得冷。
一、受冷
每年到了十二月,天气已经很冷,等到过了“冬至”这个节气,就要“进九”,以九天为单位,用谚语来描述气候在八十一天里的变化。中国幅员辽阔,描述“进九”之后气候变化的谚语有很多版本,里陂上村关于“进九”的村谚,和我们在小学课本里读到的不一样,和我看到过的其他版本也不一样。村民说的版本是:
一九、二九,相团不出手。(双手插在袖管里取暖)
三九二十七,檐墙脑上倒挂笔。(屋檐上挂着冰棱)
四九三十六,黄泥岭上长白肉。(下雪了)
五九四十五,冷得黄狗呜啊呜。(黄狗冷得呜呜叫)
六九五十四,讲吃不讲制。(过年只讲吃喝,不做事)
七九六十三,拜年路上脱衣衫。(天气暖,脱去上衣)
八九七十二,黄狗停荫树。(黄狗躲到树荫下)
九九八十一,个个脑上戴麦笠。(人人戴上斗笠遮阳)
我到农村的时候,带了一条咖啡色的“卫生裤”,有点像运动员冬天穿的厚厚的运动裤,在冬天穿上它很暖和。可是我不久便发现,穿了卫生裤以后没法卷裤腿,在寒冷的早春,要下水田的时候很不方便。
村民们看见我穿这么厚的裤子,一开始他们很羡慕地说:“过去有财主人家穿毛裤(棉裤),现在你的裤子比毛裤还要好。”等到我卷不上裤腿了,他们转而嗤嗤地笑起来:“老夏,脱了吧,脱了吧,要不然你下不了田。”他们好像是想看我在冷天的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呢。结果这条卫生裤穿了没几次,我宁愿受一点冷,也不好意思再穿了。我改穿棉毛裤外加单裤,棉毛裤的罗口拉到膝盖上,不会往下掉。
有一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我和村民张寿仁在一起聊天。他说起自己前几年过世的父亲,生前很多年都是只靠一条单裤就过冬。我说:“在屋里可以烤火取暖,这有什么希奇?”
寿仁说:“可是他还要上山挖柴根,出门挑井水,正月底就开犁下水田,都只穿一条裤。不过他也只有一条裤可穿。”
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只穿一条单裤过冬是什么感觉?我想试试。现在刚刚是腊月,这两天外面也没有结冰。”
“老夏,你真的要校验一下?
“我真的想试一试。”
第二天早上,我只穿一条单裤(当然比村民多穿一条短内裤),开始了我的受冷之旅。首先是要把水缸装满水,因此我必须出门挑水。我挑着空水桶一出门,哎呀,少穿一条棉毛裤就是不一样,冷风直往裤子里灌,很快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穿裤子一样。我一路小跑冲到井边装满一担水,赶紧迈着小碎步跑回家,倒完水以后把扁担一扔,蹦跳着跑到火塘边烤火取暖了。
接着要去自留地摘菜了,我也是蹦跳着一溜烟到地里,以最快的速度摘菜,然后匆匆回家。我一跳进门,把装菜的篮攀放在一边,先去烤火,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
就这样,我穿着单裤过冬,坚持了十几天,算是尝到了过去里陂上村穷苦人家过冬的滋味,实验便结束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冷得勾头缩颈、跳进跳出的怪样子,在旁人看来一定十分可笑。
每年春天,村里会在不同的水塘里放入鲢鱼、鲩鱼和胖头鱼(鳙鱼)这三大家鱼的鱼苗。经过二到三年,鱼儿长大了,到了冬天过年时节,生产队就会选一口水塘,干塘捉鱼,把鱼分给大家过年。
当抽水机把水塘里的水差不多抽干了,在鱼儿到处往上乱蹦的时候,我们就把裤腿差不多卷到大腿根,冲下塘里去捉鱼。我在冰冷的水和塘泥里最多只能坚持两三分钟,就要赶快上岸,拖着冻得紫红的双腿,在水塘边的火堆旁烤火取暖,过几分钟再冲下塘去。
水塘边围着很多人,几乎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来了,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只有最强的男劳力才下塘捉鱼,捉到了鱼就往岸上扔,有人会把岸上的鱼集中起来。别人捉到三条鱼了,我才捉到一条。岸上看热闹的人会高兴地喊:“老夏捉到鱼了!”我冷得嘴里咝咝地在抽气,心里却油然生出了温暖和喜悦的感觉。
里陂上村属于田多人少,每逢农历的正月底二月初就要开始春耕。如果遇上倒春寒,水田里偶尔还会有薄薄的冰茬。
这时候去犁田(村民叫耖田),就不像捉鱼的时候那样可以上岸烤火,只能咬着牙坚持。耖田半天下来,小腿以下在水里的部分冻成了紫色,已经麻木了。
我一直记得,有一天我耖田收工的时候,我把牛脖子上的牛轭解开了,整理好,又在田头把犁具洗干净了,然后用镢头挑着牛轭和犁具,牵着牛回村。说是牵着牛,其实是牛走在我前面,我的右手控制着肩上的犁具,左手握着牛绳。
牛突然停了一下,在我的面前拉了一堆屎。我一脚踩进了牛屎,一阵温暖沿着脚底往上传,舒服极了。牛还要往前走,它也想早点回家呢。我把手里的牛绳紧紧拉住,让牛停下了脚步,为的是我的双脚可以在牛屎里多享受几秒钟的温暖。
与此同时,在我身后的小路上的其他村民也不得不停了下来。他们的活计要轻松很多,大部分人是在铲田墈和筑田塍。
集体的耕牛都分散地养在各户人家。村里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早春时节,凡是养牛的人家,都要派人去耖田。妇女不用去耖田,去的全部是男人,大多数是各户人家的顶梁柱。他们是关键时刻必须走在前面忍受寒冷的人,是要担当责任的人,也是全体村民尊敬的人。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耖田收工以后,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当然是烤火,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离火太近,以免烤坏了已经冻得冰凉而麻木了的腿脚。

一到冬天,里陂上村每户人家的厅堂里的一角,就作为烤火的火塘。火塘设在进大门后的左边或右边,周围是矮凳和矮椅。火塘里的火往往从清晨一直燃到深夜,不像煮饭蒸饭烧菜那样需要快火急烧,因此用的多数是没有劈开的一段较大的木柴,燃烧起来比较慢(燃烧速度最慢的是枥子树柴)。有时候烤火的木柴用完了,村民会临时到附近的山上去挖柴根(柴蔸)回来烤火取暖,柴根烧起来也很慢。
用木柴烤火多少会有些烟。袅袅青烟冉冉上升,穿过屋顶上面瓦片之间的缝隙,飘散而去。里陂上村的房屋,瓦片直接放在椽条上,好像和我们常州老家的房子不一样。
冬天到村民家里去串门,他们马上热情地让出火塘边的座位,招呼我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老夏,来烤火。”而不是“老夏,吃了么?”
坐下来,在火塘边烤火,大家开始聊天,东拉西扯,无所不谈。记得有一次,寿仁一边拨弄着火塘里的火,一边说:“老夏,鹿冈老俵说,三个鹿冈人,才抵得上一个永丰人;而三个永丰人,才抵得上一个南昌人;要三个南昌人,才抵得一个上海人呢,还是你们上海佬最厉害。”
“照你的说法,一个上海人抵得上二十七个鹿冈人。等你哪天当了队长,我在田里做一天工,你能给我二十七天的工分吗?”我笑着说。
寿仁也笑了,他说:“嗨,会种田有什么用?我们是农民,就是脓包的意思,农民是这世上最冇用的人。”
我心里想,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以农立国。书上说“士农工商”,农民的地位仅次于知识分子(士),历来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据说每年春天的开耕时节,北京城里的皇帝,还要到一个叫做“先农坛”的地方,去扶犁耕地呢。就连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纲领十六个字里,好像也有“扶助农工”这四个字,农民排在了工人前面。
可是实际上,农民一直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自己也认为,只有最无用最无助的人,才会来当农民。看来村民的心底里,有着千年积淀下来的深深的自卑。连我们这些天天胼手胝足,和村民在一起种田的知识青年,只是因为地域的不同,村民对我们有些“仰望”呢。
大家说累了,便眯上眼睛,专心享受烤火的乐趣。
烤火真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我坐在火塘边的矮凳上,全身放松。双手向前伸出,手心向下,感受着橙黄色跳动的火苗射出的热力,身上和手上一阵一阵地暖和起来。这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静止了,只有那成段的木柴或者柴根不时发出噼噗的爆裂声,溅起了点点的火星。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全然是一片空白,真舒服。这样的状态,有时候可以持续一个多小时。
偶尔睁开眼睛,瞧一眼脚边我养的那只黄狗,它老是跟着我,正舒服地伏在地上,和我一样,在享受着火的温暖呢。它眯着的眼睛间或一动,紧紧贴在额边的两只耳朵有时会突然竖起一只来,慢慢地转一圈。如果这时候有人推门进来,我的狗会撑起前腿,挺起上身,睁开眼睛,歪过头去瞧瞧。待它发现进来的是熟人,就摇一下尾巴,表示说它知道了,然后又懒洋洋地趴下去,侧过脸,抬起眼,怯生生地瞄我一眼,往我的脚边挪动一点,继续享受着烤火带来的莫大舒适。
可是婴幼儿在火塘边烤火,会有很大的危险。他们在矮椅上睡着以后,一旦翻身滚落到火塘里,很容易造成终身的残疾,甚至会失去生命。

后来我有机会买到上好的木炭,用木炭放在专门的火盆里烤火,这是农村最高级的烤火方法。不知道为什么,用木炭烤火会感到空气很干燥。我还常常觉得,用木炭烤火的氛围和效果不如用木柴来得好。少了木柴燃烧的明火和青烟,用木炭烤火显得比较冷清和斯文,相比之下缺少了一些热闹和原始的味道。
2000年我在美国,靠贷款买了一个很小的八十多年的老房子,房子里居然有一个可以烧木柴取暖的壁炉。
快到圣诞节了,四季如春的旧金山湾区终于冷下来了。我兴冲冲地买来了专门用来烧壁炉的木柴的替代品,放在壁炉里的铁架上,点着了“木柴”。我看着那橙黄色的火苗一闪一闪地窜动,彷佛我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里陂上村,回到了用木柴烤火的岁月。
没过几年,我居住的小城为了保护环境,有了新的规定。所有的壁炉一律不准烧木柴和木柴替代品,要使用壁炉的住户必须进行改造,只可以烧煤气。
夜深了,烤火的村民回去睡了,火堆渐渐地熄灭,我也起身回屋,已经感到有一丝一丝的寒气向我袭来。
对我来说,用木柴烤火的岁月永远过去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嗣丰
(晓歌编辑)
![[冰城灯影] 五十年前的回眸](/uploads/allimg/251220/8-2512201514324Y-lp.png)



